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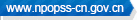
社科要聞學(xué)壇新論工作動(dòng)態(tài)通知公告最新成果集萃資助學(xué)術(shù)期刊學(xué)者傳真學(xué)者專(zhuān)欄機構設置聯(lián)系我們
項目申報與管理項目動(dòng)態(tài)成果管理成果發(fā)布經(jīng)費管理各地社科規劃管理項目數據庫專(zhuān)家數據庫歷史資料
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歷代漢文佛典文字匯編、考釋及研究”首席專(zhuān)家、湖南師范大學(xué)教授
西漢末年,佛教從印度經(jīng)西域傳入中國,對中國文化產(chǎn)生了重大的影響,這其中包括對漢語(yǔ)、漢字的影響。佛教的傳播離不開(kāi)佛經(jīng)的翻譯,而佛經(jīng)的翻譯在當時(shí)得到了高度重視。
據唐代智升《開(kāi)元釋教錄》所載,自后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(公元67年)至大唐神武皇帝開(kāi)元十八年(730),凡664年,所譯各類(lèi)佛教典籍總計2278部、7046卷。佛教的傳播同樣離不開(kāi)佛經(jīng)的傳抄。佛經(jīng)一經(jīng)譯出即輾轉傳抄,廣為流布。人們把翻譯出來(lái)的佛經(jīng)寫(xiě)在紙上、刻在石上,以此來(lái)表達對佛教的虔誠。由于抄寫(xiě)的佛經(jīng)數量眾多,加之當時(shí)使用漢字缺乏統一規范,篆、隸、行、草、楷各種字體交雜使用,人們抄寫(xiě)出來(lái)的佛經(jīng)字體風(fēng)格各異,訛字、俗字、別字眾多。許多佛經(jīng)經(jīng)過(guò)不同時(shí)期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傳抄后,變得面目迥然、異文林立。但這些變化與差異卻真實(shí)地反映了當時(shí)漢字的存在形態(tài)與使用面貌,對漢字研究具有極高的價(jià)值。正如佛教的傳入為中華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一樣,佛經(jīng)的翻譯與傳抄也為漢字的發(fā)展增添了新的元素,影響深遠,可體現在以下四個(gè)方面。
一、致使漢字的數量大幅度增加。據統計,《說(shuō)文》收字9353個(gè),《字林》收字12824個(gè),《原本玉篇》收字16917個(gè),《龍龕手鏡》收字26430個(gè),《宋本玉篇》收字22726個(gè),《廣韻》收字26194個(gè),《類(lèi)篇》收字31319個(gè),《集韻》收字53525個(gè),《改并五音類(lèi)聚四聲篇海》收字35189個(gè),《字匯》收字33179個(gè),《字匯補》收字12371個(gè),《正字通》收字33549個(gè),《康熙字典》收字47035個(gè)。中國古代字韻書(shū)不斷在增加字,這些新增的字從哪里來(lái)呢?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來(lái)自漢文佛典。從《說(shuō)文》到《原本玉篇》,漢字增加了近8000個(gè);從《原本玉篇》到《龍龕手鏡》,漢字增加了近1萬(wàn)個(gè);從《龍龕手鏡》到《集韻》,漢字增加了2.7萬(wàn)個(gè);從《集韻》到《康熙字典》,沒(méi)有增加,還減少了一些。這表明,古代字韻書(shū)中漢字數量的增加主要集中在東漢末年至宋代。我們知道,從東漢末年至宋代是佛教文獻翻譯傳抄十分頻繁的時(shí)期,字韻書(shū)恰好在這一段時(shí)期增字較多,從《字林》12824個(gè)到《集韻》53525個(gè),增加的字多達4萬(wàn)個(gè)。此后,到清代《康熙字典》,字書(shū)中的漢字數量反倒沒(méi)有增加。東漢末年至宋代,佛經(jīng)的翻譯與傳抄產(chǎn)生了大量的字,這些字不斷被字韻書(shū)收錄,從而使得字韻書(shū)的字數大增。如“傘”、“咒”、“薩”、“塔”、“魔”、“柺”、“僧”、“唵”、“吽”、“伽”、“梵”等字都是在翻譯或傳抄佛經(jīng)時(shí)創(chuàng )造的,后為字書(shū)收錄。宋代之后,佛經(jīng)的翻譯基本停滯,佛經(jīng)的傳抄也不盛行了,加之印刷術(shù)的發(fā)展,刻本文獻增多,寫(xiě)本文獻減少,漢字的數量也就沒(méi)有大的變化了。可以這么說(shuō),佛經(jīng)的翻譯與傳抄,改變了漢字數量在上古時(shí)期形成的基本格局,使得漢字在中古及近代前期在數量上有了飛躍式發(fā)展,奠定了后世漢字在數量上的新格局。
二、致使漢字的類(lèi)型更加多樣。漢字的類(lèi)型可以從多個(gè)角度歸納。從漢字的使用角度看,佛經(jīng)翻譯與傳抄致使漢字的類(lèi)型豐富多樣,不僅有一般意義上新造的漢字,如“凹”、“凸”、“寨”、“痶”等,也有為了對音梵文、巴利文等新造的一般譯音字、特殊譯音字、咒語(yǔ)字、真言字、切身字,如“嘛”、“唎”、“呢”、“袈”、“裟”等。在漢字發(fā)展史上,大規模地出現譯音字是從翻譯佛經(jīng)開(kāi)始的,而“切身字”、“真言字”、“咒語(yǔ)字”則是翻譯佛經(jīng)時(shí)的獨創(chuàng )。
三、豐富了漢字的構造理論。從古到今,人們從理論上對漢字的構造作了許多探索,在《說(shuō)文》中許慎提出“六書(shū)說(shuō)”,后來(lái)又有了唐蘭的“三書(shū)說(shuō)”(象形、象意、形聲)、陳夢(mèng)家的“三書(shū)說(shuō)”(象形、假借、形聲)、裘錫圭的“三書(shū)說(shuō)”(表音、假借、形聲)等。佛經(jīng)翻譯與傳播時(shí)創(chuàng )造出來(lái)的字絕大部分是可以用現有漢字理論解釋的。根據“六書(shū)說(shuō)”,佛經(jīng)中新造的“凹”、“凸”、“傘”等為象形字,新造的“挊(弄)”、“甭(棄)”等為會(huì )意字,新造的“塔”、“魔”、“皰”、“炷”等為形聲字。但是也有一些字無(wú)法用上述理論分析。佛典中有兩聲字,還有大量的類(lèi)化字,這些字的結構獨特,無(wú)法很好地用現有漢字構造理論解釋?zhuān)@將促使人們對漢字構造理論作進(jìn)一步的思考,完善相關(guān)論述。
四、促進(jìn)了漢字字樣學(xué)的發(fā)展。一字多形現象在漢字發(fā)展的各個(gè)階段都存在。一個(gè)字有多個(gè)形體,哪個(gè)形體是常見(jiàn)的,哪個(gè)形體是標準的,哪個(gè)形體是后來(lái)新造的,為了弄清這些問(wèn)題,字樣之學(xué)得以興起,辨別字樣的術(shù)語(yǔ)也逐漸豐富起來(lái)。《說(shuō)文》用“正”、“或體”、“古文”、“籀文”、“俗”等來(lái)辨別字樣。《玉篇》用“正作”、“俗作”、“或作”、“亦作”、“古文”、“籀文”等辨別字樣。到了隋唐,出現了顏師古《字樣》、顏元孫《干祿字書(shū)》、張參《五經(jīng)文字》、唐玄度《九經(jīng)字樣》等專(zhuān)門(mén)辨別漢字字體的字樣學(xué)著(zhù)作。這些著(zhù)作對規范定形字體,促進(jìn)文字統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唐蘭在《中國文字學(xué)》中說(shuō):“由中國文字學(xué)的歷史來(lái)看,《說(shuō)文》《字林》以后,可以分成五大派:俗文字學(xué)、字樣學(xué)、《說(shuō)文》學(xué)、古文字學(xué)、六書(shū)學(xué)。前兩派屬于近代文字學(xué),后三派屬于古文字學(xué),在文字學(xué)里都是不可少的。”與古文字學(xué)、《說(shuō)文》學(xué)、俗文字學(xué)、六書(shū)學(xué)等相比較,字樣學(xué)的研究相對滯后。佛經(jīng)的翻譯與傳抄產(chǎn)生了大量新的漢字形體,一字多樣、一字多形、多字同形現象十分普遍,這從客觀(guān)上促進(jìn)了字樣學(xué)的發(fā)展,同時(shí)也為字樣學(xué)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。玄應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、慧琳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、可洪《新集藏經(jīng)音義隨函錄》中有大量辨別字樣的術(shù)語(yǔ),到了遼代行均《龍龕手鏡》,字樣的辨別發(fā)展到了一個(gè)新的階段。《龍龕手鏡》辨別字樣的術(shù)語(yǔ)十分繁雜,有正字、俗字、通字、或體、今字、誤字、訛字、變體、俗通字、省字、今通字、籀文、古文等,至今我們還沒(méi)有發(fā)現哪本字韻中辨別字樣的術(shù)語(yǔ)比它收錄得多。弄清這些術(shù)語(yǔ)的內涵,可探查當時(shí)的正字觀(guān),對當下漢字的整理與規范具有重要意義。
佛經(jīng)的翻譯與傳抄極大地促進(jìn)了漢字的發(fā)展,漢字不僅在數量上急劇增加,而且在類(lèi)型、構造上日益豐富。漢字的這些變化直接推動(dòng)了中國古代辭書(shū)的發(fā)展,豐富了中國文字學(xué)的內涵,為當今漢字的溯源、整理與研究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語(yǔ)料和值得借鑒的內容。
(責編:實(shí)習生、程宏毅)